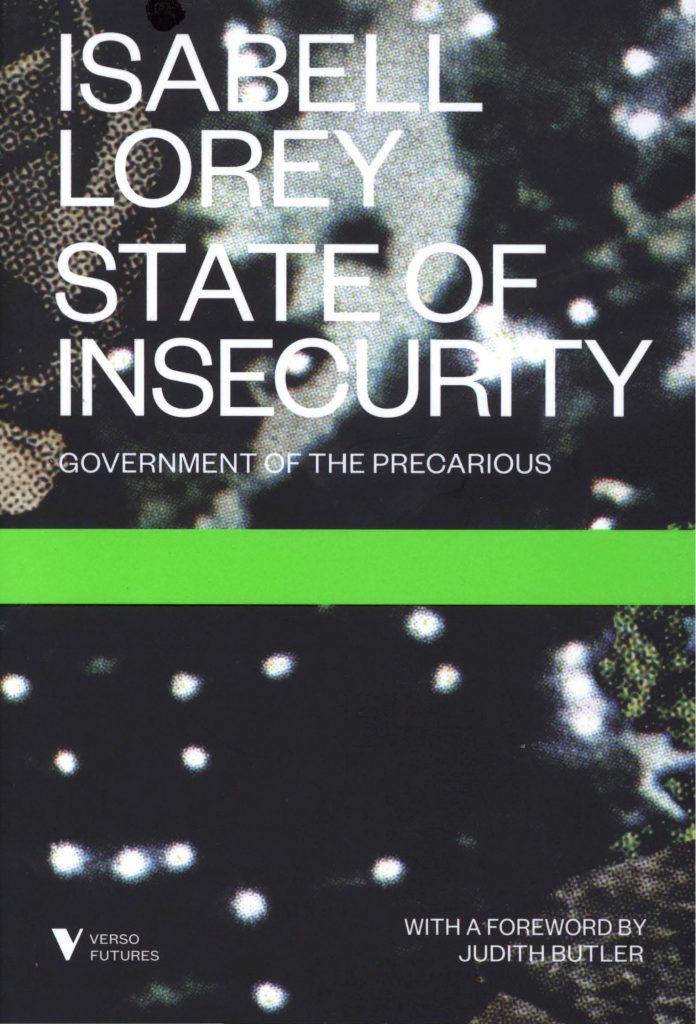
不安全状态
治理不安定者
伊萨贝尔·洛瑞
英译 艾琳·德里格
前言 朱迪斯·巴特勒
中译 麦巅
联系 incognitariat@protonmail.com 以获得全书中译PDF
前言
朱迪斯·巴特勒
这本思虑严缜之作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终得理解,不安定(precarity)并非过渡性或插曲般的一时之境,而是一种令这一历史时代殊于既往的新的规制形式。谁若断言某些人口要比其余者更不安定,并尝试解释个中差异,那么,其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要解释不安定究竟何在,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它的范围如何,它的机制又如何。事实上,要想鉴辨诸例,我们唯有求助于它更为一般的形式,而这会把我们引向思考不安定本身何以成为了一种管理体制,一种治理我们并令我们自我治理的霸权模式。洛瑞的著作让我们得以细思,一种既为福柯所预见,但又超出了他自己的权力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规制与权力形式究竟是如何成形的。显然,这份文本在许多重要酌量上都有仗于福柯,尤其是他对权力的理解:权力不但制造主体,而且也制造主体同自身的关系。但它同时也引出了新的问题:对于作为主体形成过程中一个密集权力位点的不安定及其无所不在的“不安”感,我们该作何解?换个问法:我们怎样理解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安全”的组织形式是如何将不安定当作一种生命模式,一条不定轨迹,当作一种令我们被治理、令我们开始治理自身的进程的组织原则加以要求和诱导的?
洛瑞概念极为明晰的著述,有助于我们厘清不安定的不同形式、社会影响,及其点明新的剥削权力与潜力形式的诸种特定方式。基于对政治主权的历史、马克思的再生产劳动观点的探讨,对男性自立观念的女权主义批判,以及对种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诱发性解制(destitution)的分析,洛瑞的著作就各种新的权力形式如何为着新的规制目的而汇合于当前时代,提供了一种富含历史及政治性细微差异的理解。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生命本身——在生存面向上——的短暂性或不安定,此类论断都和需求的社会与经济性结构,和——更具体地说——为了扩张安全主义(securitarian)权力形式而制造“不安”是分不开的。洛瑞的著作敦请我们密切注意“不安定化”,一种不仅制造主体,也制造作为主体之首要关切的“不安全”的进程。此一特殊之权力形式,为将安全之需确立为一种终极政治理想奠定了基底,而此一安全之需,既有利于国家与团体机构敛聚权力,同时亦制造新的主体类型。现如今,定义人口群体所依据的,不再是批判与抵抗,而是他们缓解不安的需要,这又提升了警察与国家控制形式、全球投资承诺、全球治理机构的价值。正如“金融危机”的话语能够也确实支撑了对市场加强管理性控制之必要(以及对更加专家化的资本家阶层的需要)一样,“不安定”的话语巩固了那些每隔一定时日便剑指不安定,承诺纾其困,扬言断其续的人所操纵的权力。
洛瑞的著作反思了主权教条,对阿甘本新近的主权例外观点给予了重要的重构。洛瑞将她的分析联系于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以及生命政治概念的修订,揭示了主权本身何以成为了规制人口以及人口自我规制的工具。事实上,支配主权公民概念的规范将每个人都不安定化了。他们的主权有赖于如下假定:一个人的人身或财产永远地处于外部威胁之下,而主权之实施,因此主要在于安全之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安全主义体制对人口的治理(以及因而引起的同生命政治的盘结),是通过对界定了自由主义主权公民身份观念的“防范威胁”这一基本动能的增强和再界定进行的。讽刺——如非令人痛苦——的是,主权观点必定包含不安定化,而这一点直接戳穿了有关主权独立性的传统解释的虚伪性,同时也曝露了它的内在逻辑。就晚期现代性而言,拥有主权的人民,以及,拥有主权的主体,一直为各种各样的疾病、性恐传染、犯罪潮以及形形色色的可能之侵略所威胁。于是乎,免疫(immunization)需求变得至高无上,权力则借助并通过这一需求形成了它的征服形式。一方面,主权主体具有显著的独异性,必须借助其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使之区别于群众(masses);然而,主体同它自身生命之间的关系,却显而易见地被它所业已接受,且正在将其培育成它自己的自为(self-making)实践的各种大规模的社会及政治规制形式所管理。事实上,主体对他或她自身规制越多,更具规模的规制形式也就越发奏效——这种规制形式表现为自我-管理模式,一种将乃是其根本工具的个体性(以及,培育个体之需)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式。
这本重要之作激发我们去想象能够拒食“被威胁”之饵的政治动员形式,并同那些令我们易被利用的种种恐惧保持批判性距离。实质上,洛瑞希望我们能够思索替代性方法,而不再是在将恐惧及不安全当作政治动员的基础时将其当作事实加以接受,不再进入我们被蓄意诱入,并在其中不惜一切代价求取安全的状态。如若转换焦点,注意于不安定的诱导特性,以及不安全的剥削性,将会如何?权力是被强加于主体的,但同时,权力也是主体关联自身,甚至教养自身的手段。因此,洛瑞反对一种纯粹受害化的政治(这会导致仅将权力视为是由外部所强加),反对给予“安全”(被规制主体的情感投注)以终极价值的政治。相反,她期望我们去思考那些使不安定结集,以此对抗企图强化其对人口的管理和处置权力的体制的政治动员形式——换言之,作为行动主义的不安定。参与了人口不安定化过程的新治理形式,正是通过培育主体化形式以及实践可能性而运作的,而后者能够,也必须通过不安定者的行动主义,一种与虚假的安全承诺,其管理策略,及其剥削做斗争的行动主义所拆解。
治理不安定者
导言
若失于理解不安定化,我们将既无法理解当前的政治,也无法理解当前的经济。不安定化并非边缘现象,即便是在欧洲的富庶地区。在领头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工业国家,它再也无法被外包至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外围空间,去影响那里的他者。不安定化不是例外,而是规则。即便是那些被认为长治久安的地区,同样也见到了它的扩散。它已成为一种治理工具,以及一种起着社会规制与控制作用的资本主义积累基础。
不安定化所意味的,不止是工作不稳定,不止是缺乏有薪工作带来的保障。它假借不安与危险,将整体性存在,将身体,将种种主体化模式全数包围。它是威胁,是威压,即使它同时也开启了新的生活及工作可能性。不安定化意味着与不可预见性,与偶发性(contingency)共存。
然而,在西方世俗化现代性中,曝露于偶发性,被普遍视作是噩梦,是一切保障、取向、秩序的丧失。显然,这无底深渊般的怪物,即使是在“西方”的后福特主义工业国家,也无法再被真正驯服。对无可计算之物事的恐惧,留痕于治理及主体化技术,融合成了一种度量不可度量之物事的过度文化。
这导致了一种至迟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降便不再被视为可能的治理形式:一种不通过保护与安全承诺而合法化的治理形式。相对于以服从换取保护的旧式支配规则,新自由主义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的不安全感,通过调节最低保证,同时增加不稳定性而进行。在逐步拆解并重塑福利国家以及相关权利的过程中,一种立基于通过宣称所谓的别无选择而被提升至最大可能的不安全性的新的治理形式形成了。不安定性所藉以成为治理工具的方式,也意味着它必须适度,不可越过特定临界点,否则就会严重殃及既有秩序:尤其,它断不可引起叛乱。对此临界点的管理,乃是今日治理术的构成部分。
此一背景下浮现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并终结正在推动秩序瓦解的不安定的威胁,而在于理解不安定化如何具体治理我们,并令我们自己可被治理。在分析这些治理技术时,各种想象内战、社会失范或社会解体可能性的文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助益甚微。问题的关键毋宁是,在这些治理机制当中,何处能够找到有助抵抗的裂隙与潜能。
(自我-)治理
本书中所展开的不安定分析,集中讨论了“治理”这一术语。米歇尔·福柯已经说明,“西方的”治理实践系谱可以回溯至基督教司牧权力(pastoral power)。治理人民而非物或领土的艺术,早在这一现代治理性的强力序曲中,便已经有所运用。在这一司牧形式的权力下,特定个人化模式,包括生成西方-现代性的主体,同时既是条件也是结果。个人化意味着孤立,而这种分离的实质,根本上是通过想象性关系(imaginary relationships)构建自我,构建一个人“自身的”内在存有(inner being),其次,且在较小程度上,才是通过与他者的关联构建自我。而且,这种内在性及自我指涉,并非独立的表现,而恰恰相反,是司牧服从关系中的关键性因素。 ((参见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人口:法兰西学院讲座 1977-1978》,页207-208。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与此相应的治理实践因而表现为,人在自身的行为中,正是被他者以这样一种制造与自我之间的——最好的情况下会被视为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的方式所引导。总体上而言,治理术主要在于“引导行为”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载《权力:福柯要著 1954-1984》,页 326-48,此引出自页341。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James D. Faubion, ed.,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guin Press, 1994.)),在于于他者的个人化过程中对其行为施以影响。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邪恶循环之中:一边被他者指引,一边被自我指引。“对抗以引导他者为目的而实施的进程的反引导”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人口:法兰西学院讲座 1977-1978》,页201。)) 的例子,在中世纪既已数不胜数。
十八世纪,司牧权力经历了一场根本转型:人民所不得不委身的法律不再是国王或教会的律令,而是公民自我强加的法律。这种现代的、男性的、中产阶级的主权形式所必需的,是被矛盾地(ambivalently)置于自我-决定与屈从、自我创造与服从、自由与卑从(servility)之间的各种主体化形式。就现代公民而言,如果社会与政治条件以及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被认为能够由一个人自己的(共同-)决定所安排、所影响,那么,信奉联合体,因而也对他们自己、主权、自主以及自由深信不疑的公民就会自愿地让自己服从于社会条件。
尽管如此,自我治理模式并非只是有助于令自我及他者可被治理而已。此中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不再被既有治理方式所治理,甚至越来越少被治理的潜在可能。在对通过不安全所进行的治理,即对不安定者的治理进行分析时,甚为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治理的这种双重矛盾性:存在于他者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的矛盾心理,以及,存在于自我治理之中的矛盾心理——一面是卑从,让自己可被治理, 另一面是拒绝,不让自己继续被如此治理。当我们于此书中发问,为何针对不安定性治理的抗议如此之难、之罕,我们是要对不安定者自我-治理的卑从面向显而易见的支配性进行问题化。与这一面向无法分离的,是现如今正在变成霸权的劳动形式:主要基于交流、知识及情感,以技艺劳动(virtuoso labour)这种新方式彰露的,要求人以己全部之能参与的劳动形式。
集体之危机,共通之契机
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起,并未因为劳动力的自由而获得保障,免受生存脆弱性的伤害的人,数量甚众。有薪劳动既未带来安全,亦未带来独立。 ((参见罗伯特·卡斯特,《从手工工人到有薪劳工:社会问题的转型》。
Robert Castel, From Manual Workers to Wage Laborers: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Question, trans. Richard Boyd,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唯有经过斗争得来的集体性福利-国家体制曾一度有能力确保一种基本上也仅是为男性养家者所拥有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这样一种保障形式,关系再生产以及照护工作不得不被女性化、家庭内务化,其作为劳动的性质亦遭致贬低。 ((参见薇西亚·费德里奇,《卡利班与女巫:女性、身体及原始积累》。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4.)) 当然,对男性主有的独立性所进行的安全保障也是有其益处的,那就是让具有依赖性的工人能够被组织、被聚合起来进行集体斗争。
随着新自由主义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废除与重构,以及短期的,越来越不安定的雇佣条件的兴起,在工厂或职业群体内进行集体组织的可能性也被逐步蚀化了。就业过程中已形成了新的个人化形式,它们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利益代表机构进行组织。现如今,怎样才能找到可以突破这些个人化形式的新的组织性实践?如何才能形成一种深入社会及政治境况,但又不排斥个体之间的关系、连接以及依存性的视角,换言之,形成一种对始于同他者的关联的自我-依靠形式展开想象及实践的视角?
如果不将不安定化纯粹当作是一种威胁加以理解和斗争,而是将不安定状态当作整体(ensemble)加以考量,将当前支配-安全保障功能以及主体的不安定化经验当作政治斗争的起点,这便是有可能的。
若要以此方式理解不安定化,那就有必要重新开放不安定状态的概念领域,追踪法国社会科学自1980年代初以来对它的使用中所形成的局限,以及它在其他语言所进行的相关讨论中的进路。 ((参见Precarias a la deriva,《‘好战研究’计划与方法:诸众实践反思》,载《帝国与生物政治的转折:国际论哈特与内格里》页 85-108,引文出自页93。
‘Projekt und Methode einer “militanten Untersuchung”. Das Reflektieren der Multitude in actu’, trans. Kathrin Held and Peter Tabor, in Marianne Pieper, Thomas Atzert, Serhat Karakayali and Vassilis Tsianos, eds, Empire und die biopolitische Wende. Die internationale Diskussion im Anschluss an Hardt und Negri,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Campus, 2007.)) 如果不安定化不再被局限于缺乏、强制与恐惧,那么,对一种简单的“去不安定化的政治” ((克罗斯·杜瑞,《无保障的劳动社会:去不安定化的政治》,载《矛盾》杂志第49期,《社会主义政治》,页5-18。
Klaus Dorre, ‘Entsicherte Arbeitsgesellschaft. Politik der Entprekarisierung’, Widerspruch. Beitrage zu sozialistischer Politik 49 (2005).))的要求也就不再合乎情理了,因为它所寻求的,无外乎是重构传统的社会-安全体系。依我所见,只有在它能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霸权政治与社会安全逻辑问题化并有所突破,只有不安定与不安定化作为支配工具的诸种功能能够因此得到分析,并最终,只有在辨识一种无可避免的不安定性状态过程中能够找到针对不安定及不安定化的新的安全与保护模式时,这种政治才会有意义。
不安定者与代议批判
国际不安定化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社会学家皮埃尔·鲍德里亚与罗伯特·卡斯特,曾于1990年代末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不安定环境下,集体抵抗将变得没有可能。 (( 参见皮埃尔·鲍德里亚,《今日处处不安定》,载《防火:抵抗新自由主义入侵的提议》,页95-101; 罗伯特·卡斯特,《社会不安全:被保护的是什么?》,页46-7。
Pierre Bourdieu, ‘La precarite est aujourd’hui partout’, in Contre-feux. Propos pour servir a la resistance contre I’invasion neo-liberale, Paris: Liber – Raison d’Agir, 1998; Robert Castel, L’insecurite sociale, Qu’est-ce qu’etre protege? Paris: Seuil, 2003.)) 卡斯特虽然注意到了包括跨国性“欧洲五一日”(EuroMayDay) ((若想简单了解欧洲五一日运动的历史,可参见杰拉尔德·劳尼格,《千机器:作为社会运动的机器的哲学纲要》,页75-90。
Gerald Raunig, A Thousand Machines: A Concise Philosophy of the Machine as Social Movement, trans. Aileen Derieg,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0.)) 在内的不安定者运动,但他涉入甚浅且相对迟晚,鲍德里亚则甚至都没能睹上一眼。 ((参见罗伯特·卡斯特, 《社会不安全的回归》,载《不安定、出身、排斥:21世纪初的社会问题》,页21-34。其中卡斯特提到了法国文化工作者或者临时工(Intermittents)。
Robert Castel, ‘Die Wiederkehr der sozialen Unsicherheit’, trans. Thomas Atzert, in Robert Castel and Klaus Dorre, eds, Prekaritat, Abstieg, Ausgrenzung. Die soziale Frage am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Campus, 2009, pp. 21-34.)) 他于2002年初辞世,距2001年5月米兰首次“五一游行”尚不足一年。在这一传统的劳工节日里,欧洲许多城市中异质性的不安定者将他们所不怎么为社团主义组织理睬的境遇及经验问题化,并从批判身份及代议的政治实践着手,探寻新的组织形式,以组织起难以组织的劳动群体。 ((参加《文化:激进民主文化政治杂志》》杂志第四期,《组织难以组织者》。
Kulturrisse. Zeitschrift fur radikaldemokratische Kultur-politik: ‘Organisierung der Unorganisierbaren’ 4 (2006), available at http://kulturrisse.at.)) 为了找到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政治介入的可能性,不安定的工作及生活条件被当作了政治抗争的出发点。
这些社会运动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其试验新的政治抗争形式,以及深化新的不安定化视角的方式。同时,它们还同看似大不相干的文化及政治领域反复进行了横截交叉——这一点,相较于其他社会运动,尤有冲击力。过去十年间,围绕着与不安定相关的,具有某种颠覆性的知识所进行的交流,以及为找到有助于政治创制(constituting)的共通点而进行的沟通调研,更为频繁地发生于艺术机构及社会中心(譬如意大利与西班牙),而非政治,甚至大学语境。这仅是新聚集及组织模式探寻及发明过程中的一个面向,而它们的传统模式,正如鲍德里亚和卡斯特所准确指出的,已难再奏效。
不安定者无法被统一或者代表,他们的关注点如此迥异,以致传统的社团组织形式难有作为。大多数不安定者都处于分散状态,这既体现于生产关系,也体现于多样性生产方式,后者吸纳并酿成了不同的主体性,深化了对他们的经济剥削,多重化了他们的身份及工作场所。不安定的,分散的,并不只是工作,生命本身亦是如此。不安定者群貌繁多,容易被孤立,被个人化,这是因为他们做的是短期工作,辗转于不同项目之间,往往都无法进入集体性社会安全体系。多样化的不安定者们既没有专门的游说团体,也没有专门的代议形式。
但绝不可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纯粹的缺乏,这是因为它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即,基于不安定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发明新的、适合的政治介入形式。“五一”运动的着力之处,并不在于为一种集体性的不安定主体代言,而是在于对非代议实践进行实验。就此而言,不安定者运动可谓是2008-2009年大学占领、当前占领(Occupation)运动及其所坚持的超越代议制的民主主张的先驱。保罗·维尔洛写到,“后福特主义诸众的一个特点,是挑衅政治代议制,令其崩溃:并非一种无法无天的姿态,而是一种冷静地、现实地探寻新政治形式的手段。” ((保罗·维尔洛,《智识的公共性:非国家公共空间与诸众》,载《横截线:公法》。
Paolo Virno, ‘Publicness of the Intellect: Non-State Public Sphere and the Multitude’, transversal: ‘Publicum’ (June 2005), availa-ble at http://transversal.at. ))
“五一”运动中,“不安定”(precarious)概念的不同意义被反复地关联于个体经验以及政治实践经验。“弗拉萨尼托网络”(Frassanito Network)在其对不安定的定义中,勾勒出了这一术语令人矛盾的面相,尤其是在移民的语境中:“不安定化因此象征了一个争夺领域:此一领域中,开始新一轮剥削的企图,遭遇到了拒绝旧有的、被谓之后福特的劳动体制,转而寻求另一种更美好的,我们甚至可谓之灵活生活的种种欲望及主体行为。” ((弗拉萨尼托网络,《不安定者、不安定化、不安定阶级?》
The Frassanito-Network, ‘Precarious, Precarization, Precariat?’ (2005), available at http://thistuesday.org. ))在不安定化过程中,一种程度极端的剥削与一种脱离传统的、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捆绑在一起的剥削条件的“解放”,一同并入了各种新的主体化形式当中。
不安定者的三个维度
“不安定的”的概念构成,在最宽泛意义上,可被描述为不安全及易伤性、去稳定化及危害性。与“不安定的”相对的,通常是保护,是旨在对被认定为具有致害性的所有一切进行防范的政治及社会性免疫。 ((有关“免疫”这一术语所涵盖的不同保护及威胁动力,可参见伊萨贝尔·洛瑞,《免疫形式:政治理论原理》。
IsabelI Lorey, Figuren des Immunen. Elemente einer politischen Theorie, Zurich: Diaphanes, 2011. )) 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保护自己免于不安的政治观念,并非完全只是拜霍布斯所构想的安全国家所赐,在后者的观念中,代理主权者负责防御所谓的人之自然状态,而危险他者对财产及生命的破坏就内在于此一状态之中。防范不安全,防范不安定者,同样也是二十世纪福利国家的责任。 ((参见卡斯特,《社会不安全》。)) 然同时,无论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还是福利国家,都没有阻止不安定,反倒是分别地引致了不安定的新的历史形式,新的不安全,而它们反过来又使得前者有责任提供更多保护。
普遍而言,那些被给予安全承诺的人,并不能摆脱对具有威胁性的,被不安定化的他者的焦虑而无忧发展;他们有义务听命及顺从。因此,不安定者,以一种具有历史性差异的方式,同时代表了支配及安全的理由与效果。
然而,当后福特社会中支配的合法化不再是通过(社会)安全,而是如我们所经历的,通过不安全性治理时,不安定者与免疫系统、不安全与安全/保护在对立关系上逐渐弱化,而在(仍)可治理的管制性临界点方面,则逐渐呈现出一种渐变关系。此一动态的一个关键基础,是新自由主义中的不安定化当下的常态化进程,不安全性治理通过它而得以施行。在新自由主义中,不安定化变得“民主化”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些论点,我在不安定者的三个维度之间做了区分:不安定性(precariousness)、不安定(precarity),以及,治理性不安定化(governmental precarization)。
不安定性——这里我采用了朱迪斯·巴特勒的定义——是一个表示生命及身体的社会-本体论维度的术语。 ((参见朱迪斯·巴特勒,《战争之框:生命何时可悼?》;巴特勒,《不安定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and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不安定性并非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恒量,一种超历史的人类存在状态,而是一种无论人类抑或非人类都会与生俱来的状况。然而,究其竟,不安定性并不简单是个别性的,或说是某种哲学意义上的“自在”(in itself)之物;它从来都是关系性的,因此,它从来都是和(with)其他不安定生命所共同具有的。不安定性指的是某种存在意义上的共通状态,一种针对身体的,无可避免因此也无法预防的危害,这不仅仅因为它们是致命性的,更因为它们是社会性的。作为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意义上的不安定“共-在”(being-with),不安定性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处境,它在不同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中产生了殊然迥异的种种变体。 ((见让-吕克·南希,《独一复多的存在》。
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t D. Richardson and Anne E. O’Byr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不安定者的第二个维度,不安定,将被理解为一种包含了针对普遍不安定性的政治、社会及法律性弥补所获效果的秩序范畴。不安定指的是不安定性在不平等关系中的条痕(striation)与分布,伴随着他者化进程的“共-在”等级化。不安定者的这一维度涵盖了一种自然化了的,决定个体是否归属于群体的支配关系。不安定包含对不安全进行的各种社会定位,但它并不必然导致被定位者的主体化模式,亦不必然导致其能动力。
不安定状态的第三个维度是治理性不安定化动能。它同工业资本主义条件形成以来所出现的治理模式有关,而且,在现代西方社会,它同中产阶级主权这一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历史关联。
尽管不安定性同时指明了一种生命条件,以及社会性存在(the social)及政治性存在(the political)的基础,但直到生命——随着如福柯所分析的,在十八世纪晚期及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政治——进入政治时,这种治理才开始以一种前所未知的方式,将重心置于维持人口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以此来强化国家力量,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 ((参见福柯,《知识意志:性史》,卷一,页141;洛瑞,《当生命进入政治:生物政治治理的现代性:福柯与阿甘本》,载《帝国与生物政治的转折》,页269-92。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trans. Robert Hur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Isabell Lorey, ‘Als das Leben in die Politik eintrat. Die biopolitisch-gouvernementale Moderne, Foucault und Agamben’, in Pieper et al., eds, Empire und die biopolitische Wende. ))在这一新的治理艺术的进程之中,可治理性生命政治主体化出现了。十八、十九世纪,生命政治主体化渐趋紧密地同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自由以及民主自我决定论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治理性不安定化不仅意味着在就业中去稳定化,也意味着对生命行为,继而对身体行为,对主体化模式去稳定化。将不安定化理解为是治理性的,使得有可能将发生于治理工具、经济剥削条件、主体化模式之间的,发生于他们的屈服与自我培力的矛盾性之中的复杂互动问题化。自我培力实践并不自动地带来解放效果,而反倒是——若从治理视角来理解——彻底矛盾性的。它们所说明的可能会是代表了一种使得超常可治理性成为可能的从众性自我发展、从众性自我决定的种种自我治理模式。当能,培力实践也可能会突破、拒绝或逃离正在运行中的自我治理的吸引力。
在治理视角中,对不安定性的考量,不仅可以依据其种种压制性的,条痕化的形式,亦可依据其矛盾性的——正如那些经由自我治理技术所形成的——生产性时刻。在这样一个偶发性并不只是以新的方式隶属于经济剥削条件的历史时期,治理性不安定化这一术语还可以涵盖一种处理不可计算之事物、不可被度量或模组化之事物、避开了不安全性治理之事物的生产性方式。
不安定者的这三种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独自出现的,而是出现于具有历史性差异的假定关系之中。根本上,它可谓是存在于不安定性-不安定之间,引致了不同支配形式的关系。其社会-本体论层面被构建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必须防御,必须免疫的威胁。一般而言,对部分人的保护的合法化,需要对那些被标识为“他者”的人的不安定进行条痕化。尤其是这一点,令自由主义治理性的机杼相当特别。具有威胁性的不安定性能够被利用来建构危险他者,被分别当作“反常者”(abnormal)及“异族”(alien)置于政治及社会共同体的内部与外部。如前所指,在新自由主义中,不安定化正处于常态化进程,此中,尽管自由主义对不安定的赋序模态仍以一种修正过的形式存在,但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定性再无可能通过构建危险他者而被完全转换,被当作不安定加以完全隔离;相反,它是在对那些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被常态化者进行个人化的治理性不安定化中实现的。
在研究不安定者治理的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对一种始于同他者的连接性,将不安定者的不同维度皆纳入考量的政治及社会理论视角进行深化。有鉴于每一种(生物)存在都具有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安定性,将社会关系性视为基础,并不表示出发点是某种所有人均等共有的东西。对社会关系性的认识,仅能被当作是进入各种生成—共同(becoming-common)进程的起点,而这需要对不安定者的相异性中所可能具有的共同利害关系进行讨论,以此同他者一道,发明在拒绝服从中突破现有治理形式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秩序。
2012年3月,柏林
